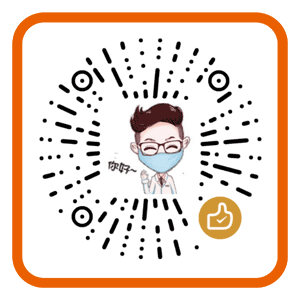关于读书与写作,止庵有一本《沽酌集》,成书于作者不惑之年,距今已经有二十年了。书中所收文章大多与书有关,或是书人书事,或是书评随想,读书为主,兼谈写作等。虽是旧文,读来仍觉新鲜,虽一家之言,却很有一番意趣。他在《序言》中谈到书名的由来:
“沽”,买酒也;“酌”,饮酒也。我取这个题目,好像做了酒鬼似的,其实不然。打个比方罢了。平生兴趣甚少,烟酒茶均不沾,也不喜欢什么运动,只买些书来读;但我觉得就中意味,与沽酒自酌约略相近。若说不足与外人道未免夸张,总之是自得其乐。至于偶尔写写文章,到底还是余绪,好比闲记酒账而已。(《原序一》)
有人说:
读止庵文章,有种“操千曲而后晓声,观千剑而后识器”的感觉。
读《沽酌集》是怀着“难能可贵”的信念去理解的,有种学生时代学白话文的心情,带着点苦恼,却纯粹简单。
《沽酌集》里所谈的书与作家,古今中外皆有,尤其对于日本文学,见识不同于流俗。
《沽酌集》中,作者所读书籍看似无直接联系,却用其独立的思考和直白的语言向人展示出阅读的魅力。
《沽酌集》无任何矫饰,冲淡而洗练,舒展自然中见性情,内敛平淡中见积淀。
止庵自己则评价《沽酌集》:以读书之作论,大概我以往写的书中,以这本为自己最满意。
《沽酌集》是一本“小书”,书不厚,字不多,收录止庵文章,却有54篇之多。这本内容丰富的小书从古到今,不论中外,臧否人物,漫谈世事与学理。书中究竟展示了止庵怎样的读书作文经验和追求?不妨翻开这本《沽酌集》,读一个别处读不到的止庵。
从古到今,不论中外
片断随笔,考据文章
撰写民国文人掌故,梳爬史料再整理
鲁迅 周作人 张爱玲 钱玄同
刘半农 徐志摩 废名 钱穆
漫谈外国文人名作,分享审美意趣
清少纳言 川端康成 谷崎润一郎
穆齐尔 尼米埃 莫里亚克 塞利纳 达利
梅列日科夫斯基 霍达谢维奇 扎米亚京
读书为主,兼谈写作等
那么姑且不论对错,只对活过的年月稍事回顾罢。说来无非读书、写作二事。(《新序》)
从根本上讲,我把阅读视为对于真理和创造的一种认同过程。所以一再声明,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读书,偶尔记录感想,不过是副产品罢了。(《关于自己》)
我们常说“开卷有益”,其实“益”往往只在“开卷”,然而已经足以使我们去读书了:多知道点儿此前不知道的东西,有什么不好呢。(《思考起始之处》)
假如当初不读这些书,自己会是另外一个人;因为读了这些书,方才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。(《关于自己》)
读别处读不到的止庵
去法国韦桑岛时,每逢吃饭,面对菜谱总是茫然,只好对服务员以手示意(我不懂法语,他们不懂英语):和邻桌的人吃的一样。于是接连三顿,都吃一种加入少量洋葱煮的贝类(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道菜叫什么名字),再好吃的东西也倒了胃口。到第三天,我正吃着,终于有位顾客走过来, 用英语问我需不需要帮助, 大概实在看不下去了罢。然而我已无须什么帮助,因为马上就要离开这岛了。但不知是感动还是兴奋,我请他喝了一杯啤酒。(《饮食行》)
日常生活,服饰时尚,旅行饮食,
读止庵生活中有趣可爱的一面。
止庵先生谈读书,非人云亦云、不就书论书,而是发散开去,结合人生阅历、世情世事,说些自己想说的话,读些别处读不到的东西。
从“必读书”谈起
前些时偶然读到一九二五年《京报副刊》上几则“青年必读书”,觉得很有意思。这件事情迄今仍被提及,多半因为鲁迅有名的回答:“从来没有留心过,所以现在说不出。”多年后,周作人在私人通信中说:“‘必读书’的鲁迅答案,实乃他的‘高调’——不必读书之一,说得不好听一点,他好立异鸣高,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,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,却是十分简要的。”(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致鲍耀明)鲁迅的举动,在我看来更接近于现在所谓“消解”,针对的是“青年必读书”中的前提设定,即那个“必”字;以及因诉诸公共媒介而对价值取向的一种规范。但是一般论家往往只看到他拒绝回答,却忽略了他能够回答。鲁迅所开书目即《开给许世瑛的书单》,载《集外集拾遗补编》。我们看了,不能不佩服其别具只眼而又精当,的确是为学习中国文学指点了一条路径。虽然我想终鲁迅一生,他都是反对设定前提和规范价值取向的。这是鲁迅的伟大之处。1936年10月,鲁迅与青年艺术家们从另一方面看,鲁迅真有这个本事;而这往往是后人(包括学者在内)所欠缺的。我们学得了他拒绝回答,却未必学得了他能够回答。一旦试图做后面这件事情,欠缺也就暴露出来。曾在报上看见一份“为初学者开列的中外文学书目”,开列的人读书实在太少,简直成了笑话。还有报纸辟过“我心中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”专栏,读者的回答却多是“我眼中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”,除了所说的好像没有读过多少别的。两件事情是同一道理。在一切关于书的文字中,书目大概是最难写的,必须要有真本事:第一是足够的阅读量,第二是高明的选择能力。二者缺一,这件事情就干不得,而前者是为后者的基础。书目内容越少,就越不容易,因为并不意味着阅读量可以减少,只是要求选择能力更强罢了。前述“文学书目”打算包罗古今中外,不啻自不量力,我们哪里还有这样的通才;能就其中某一部分开列个像样的单子就不错了,但是尚未见到。类似康诺利《现代主义运动》和伯吉斯《现代小说佳作九十九种》那样的书,不知道是否有学者能写得出来。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书目实际上是文学史的雏形,至少其中体现了撰写者完整的文学史观。 一本文学史实际上就包含着一份书目。那么前述撰写书目必备的本事,也该为文学史的撰写者所具有。讲到文学史,似乎只与作者有关,而与读者相远,其实不然。我们平常读书,之前加以遴选,之后有所评价,有所比较, 这里已经孕育了文学史的观念。夸张一点说,一切文学评论都是文学史,当然反过来一切文学史也都是文学评论。曾经有过很有分量的文学史著述,譬如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和周作人的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。胡适的《白话文学史》虽然稍嫌偏颇浅露,毕竟自成一家之言,他确有一个“主义”支撑局面。刘大杰的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(初版本),就整体而言大概是这方面最后的个人之作了,当然他也受到鲁迅、周作人和胡适等人很大影响。现在重读这本书,我们不一定完全赞同他的看法,但是不能不佩服他的宽容态度。他说:“站在客观的立场来写文学史的人,必得要分析各派的立场,理解各派的特色,才可得到比较公平的结论。”所以对并不合他本意的李贺、杜牧和李商隐等人之作,也能看出特别的好处。一部文学史,除视野必须开阔,资料必须充分外,最不容易也是最重要的是,它应该既是个人的,又是客观的。这个意思,约翰·玛西在《文学的故事》中也说过:“什么是重要的?这是每个人——如果有能力的话—必须自己来回答的问题;而另一方面,这个问题又被一致的公论所决定。然而,公论的决定也不是绝对的。”公论与其说是公众的论,不如说是公正的论;个人见解达到客观,庶几近乎公论。此后的几部文学史(包括刘氏对自己著作的修改),在丧失个人见解的同时也丧失了公论。客观不是非个人立场,而是不以个人为唯一立场。时隔多年,终于又有融公论于个人见解的作品面世,陈平原的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》即为其中之一,可惜此书离最后完成差得还远。陈氏的著作未及完成,这里不便多加议论;但是有一点大概没有问题,就是这本书越往后写,将会越困难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成功的文学史都是距离之作。这样公论才有可能被确定是公论,而个人见解也才有可能被确定是不违背公论。所以我对当代文学史的撰写一向有点儿怀疑,因为实在很难分得清是非轻重。历史原本是人所留下的不能磨灭的痕迹,现在可能只不过是地上一些影子而已;待到这个人离去,影子也就没了。初、盛唐人若是写文学史,恐怕会取上官仪舍初唐四杰,对沈、宋的评价也在陈子昂之上, 而杜甫也不会像以后那样备受推崇。“什么是重要的?”真要回答恐怕还得等一等。前些时《郭小川全集》出版,论家对他的诗作积极评价,所根据的却主要是个人当年的阅读记忆。这虽然不是在写文学史,但是不妨直截了当地说文学史不是这种写法。文学史基本上是排斥当事人的,因为对某人某时重要,并不意味着对历史重要,何况这个历史还是文学史。文学史最终有着属于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,前述个人见解也好,公论也好,都离不开这一前提。这里涉及一个“时代代表”的说法。如果尚未搞清时代的本质,怎么推举谁是代表;就算真能代表,这也是个社会史而不是文学史的概念。很多话我们可以拿到别的场合去说,而文学史允许空白,假如当时文学确实没有成就的话。杨绛的《干校六记》
宽容是在承认自我的前提下对自我有所限制。公正始于宽容, 不宽容则容易流于党同伐异。《书屋》今年第三期刊载的《五十年: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》,可以被认为是撰写文学史的最新尝试,但是也不过是尝试而已。例如谈到杨绛的《干校六记》时说:“在这里,杨绛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党人的后裔那遗留在血统中的一点精神。 但是,全篇的行文是简淡的。 大约这就是所谓‘寄沉痛于悠闲’ 罢。而这种为中国文人所乐用的叙述风格,恰恰是消解沉痛的。”真正的文学史总是能够容忍风格的,一个文学史家与一个读者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;虽然文学史家首先应该是个好的读者。而此文提示我们,即使这一点也很难做到。作者眼光停留在文字表面而不肯深入体会,仿佛不知道“相辅相成”之外还有“相反相成”。容忍风格才能理解风格。更重要的是,个人见解很有可能像非个人见解一样排斥公论。不宽容的个人见解,对于文学史来说不仅算不上优点,而且充满危险意味。统一于某一个人见解,与统一于非个人见解,其间没有任何区别。二〇〇〇年四月十八日
话说两种读书态度
前两天我去上海,在机场的书店里,看见有关这回经济危机的书出了不少,还在显眼之处摆成专柜。这让我想起从前闹“非典”,加缪那本已经译介过来多年的《鼠疫》一时成了热门书。 大概这是我们一以贯之的读书态度罢,尚未脱出某篇曾经鼎鼎有名的文章里所说的“要带着问题学,活学活用,学用结合,急用先学,立竿见影,在‘用’字上狠下功夫”。我在出版社工作时,也常常听说出书要“赶热点”,而这正因为大家读书往往是要“赶热点”的。加缪当然也有例外。张爱玲在《烬余录》里写到日军侵占香港时,“在炮火下我看完了《官场现形记》。小时候看过而没能领略它的好处,一直想再看一遍。一面看,一面担心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。字印得极小,光线又不充足,但是,一个炸弹下来,还要眼睛做什么呢。—‘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?’”李伯元几十年前写的《官场现形记》,显然与张爱玲那时的处境毫无关系。《官场现形记》
我觉得如此才得读书真谛,读来也才有意思,才能真正“领略它的好处”。——我们常说“开卷有益”, 这个“益”不能理解得太现实了。当然对于前一种读书态度也犯不上反对,即使反对也没有用处,我敢肯定经济危机将是“二〇〇九年社科图书阅读热点”,只希望不要一窝蜂地都盯着这个就是了。讲到读书, 这几样必不可少: 一是有书可读—买,借,或在书店里“蹭”书看,都行;二是要有时间;三是要有精力;四是要有兴趣—对书的兴趣和对某一本书的兴趣;五是要有心得—读一本书,无论正面反面,总归有点收获,不然岂非白搭功夫。以此来看“在(经济)危机下阅读”,大约只有头一项多少沾点边儿,亦即因为经济危机而找不着工作,或丢了差使,减了薪酬,没钱买书,以致影响阅读—这种事儿自己暂且还没赶上,也就不能说什么,其余似乎都与“危机”与否无关。所以书照样还是读得,而且想读什么就读什么好了。要我来推荐几种今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方面的新书,自无不可;但我还得重复一下说过的话:出版界面对的是现在的读者,读者面对的却不只是现在的出版界——他不一定非读新书不可;迄今为止出版的书,只要能找到的,都在可读之列。真正读书的人,什么书好才读什么书,并非什么书新才读什么书。二〇〇九年四月七日
以上两篇文正选自止庵《沽酌集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10月止庵作家、学者。有《惜别》《画见》《周作人传》《神拳考》《樗下读庄》《老子演义》《插花地册子》等著作,并编订周作人、张爱玲作品。
作者: 止庵 出版社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出版年: 2020-10 页数: 344 定价: 59.00
《沽酌集》收录止庵文章五十四篇,大多与书有关,或是书人书事,或是书评随想。书中既有对周氏兄弟、张爱玲、废名、钱穆等现代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品评与考据;也有对日、法、俄等外国文学、历史、艺术作品的赏读;更有说“文心”的篇目,兼谈作者买书、读书、写书、编书的心得。从古到今,不论中外,臧否人物,漫谈世事与学理,舒展自然中见性情,内敛平淡中见积淀,很好地诠释了“把阅读视为对于真理和创造的一种认同过程”的阅读观。
点击下图微信预定2021年《天涯》
天涯微信号:tyzz1996
-投稿邮箱-tianyazazhi@126.com
Frontiers
作家立场|民间语文|文学
研究与批评|艺术|……
WRITERS' POSITION
POPULAR VOCABULARY LITERATURE